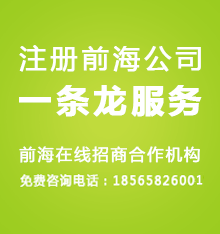以法治引領深圳和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的
責任編輯:前海自貿區政策專員更新時間:2019-07-01 16:30點擊:
“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引領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參與國際合作”,進一步為深圳和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的深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其中明確提出了“構建極點帶動、軸帶支撐”的網絡化灣區空間格局,特別是“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引領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參與國際合作”,進一步為深圳和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作為珠三角主要的城市發展極點,深圳和香港特區歷來就具有深度融合的基礎,不僅探索建立了深港兩地政府常態化會晤機制,就聯合建設粵港澳更緊密合作區的有關問題進行深入交流,還將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不斷發揮引領帶動的作用,成為灣區乃至全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一、深港合作的良好基礎:從產業轉移到深度融合
早期的深港交流始于貿易領域的合作,以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區為標志,香港開始將制造業大量轉移至人力資源豐富、亟需發展的深圳,深圳成為承接香港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地域,逐漸形成“前店后廠”的合作模式,并使得出口貿易成為深圳的主要貿易模式。直到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簽署,深港合作開始逐漸擺脫低端的“三來一補”模式,高端制造以及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逐漸提上議事日程。
2011年,深圳市“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深港融合”的思路,將深港合作與發展關系推上了新的階段,并在前海正式設立合作區,切實發展深港融合,開始從產業、金融到法治政府、司法改革、制度建設等領域的全面合作。2012年6月29日,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復》,提出“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打造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務業發展集聚區、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區、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的引領區”。2015年,前海蛇口片區納入廣東自貿區之后,政策疊加的優勢逐漸顯現,前海在促進深港融合方面一直積極探索,力爭以政策的疊加優勢和法治創新本身最大程度釋放改革紅利。
二、深港深度融合的制度基礎:法治是最大公約數
深港融合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兩地政府合作深化、共同推動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深港兩地的利益訴求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尊重,兩地的經濟發展需要實現了互補。但更重要的是,深港融合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發展過程,是市場自發的合作逐步向政府和公共層面不斷提升的過程,這一過程實現了市場和政府的良性互動,有利于在宏觀層面更有效地推動深港兩地經濟社會資源的全面整合,以彌補市場機制可能出現的不足。深港融合是從市場機制到法治建設全面拓展和深化的過程,由具體的工廠合作到產業實現互補,由產業協調再到框架協議指引,由框架協議再到國家政策,這一系列的融合過程,實質上是兩地制度不斷創新的過程,也是深港兩地由單一合作走向全面融合的過程。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的法治城市建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而香港特區整體法治水平在全世界都處于領先地位,兩地融合實際上具有國內最為堅實的制度基礎。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融合的背景下,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深圳積極向香港特區治理的先進經驗學習,不斷加大引進香港特區先進制度的力度,例如前海管理局即是我國首次借鑒英美法系成立的法定機構,還吸納了蛇口企業和咨詢委員會等社會機構作為社會化管理的嘗試,在“小政府、大社會”方面做出了有價值的嘗試。在深港兩地司法合作方面,深圳前海法院開始嘗試對接香港專業調解機構,已經成功通過港籍陪審員和糾紛調節機制審理了多項涉港案件,探索商事領域法律規則的國際化對接。此外,香港和解中心正在同前海法院建立合作,共同解決大灣區法律糾紛案件及為跨國、跨境案件尋求調解方案。2015年成立的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在深港融合的機制建設方面,通過“聯席會議+咨詢委員會+聯合工作組”常態化機制加強深港合作;以部際聯席會議、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等協調機制、金融、法律等專業咨詢委員會機制以及前海深港聯合工作組的協作機制,加強前海管理局與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前海開發建設中的溝通和協作,共同解決前海開發開放中需要雙方合作協調的問題。
三、法治視角下的粵港澳大灣區深港融合前景

三、法治視角下的粵港澳大灣區深港融合前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際上是推動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其建設和發展,需要法治先行、法治引領和法治保障。但是,由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在世界范圍內沒有現成的模式和經驗可資借鑒,諸多挑戰和機遇,對大灣區發展語境下的深港融合指明路徑。
第一,發揮法治創新的主動性。要積極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地區相關立法授權工作要及早作出安排”的指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合理運用經濟特區立法權,加快構建適應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根據深港兩地融合中的實際情況進行法律論證,切實解決政策密集出臺,卻很難落地的問題。積極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要求,結合深港融合以及法治創新中的實際問題,借助《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修訂的機會,深化前海深港合作,對治理結構進行創新探索,定期審視前海合作區管理機構的運行情況,提出對區域治理型法定機構發展的新構想,特別是解決當前前海規劃體系與深圳市規劃體系在行政管理中的協調問題。
第二,加強司法機制創新合作。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下,深港合作可進一步加強法律事務合作,特別是加強深港司法合作交流,在知識產權保護、公益訴訟等領域探索,建立與粵港澳大灣區深港融合發展相適應的司法體制。例如,前海法院在業已建立的“精英法官+港籍陪審員+專家咨詢”的專業審理機制下,進一步優化由域內外金融保險、國際貿易、知識產權、證券期貨等領域專家組成的專家智庫,對復雜疑難案件提供專業咨詢意見,促進案件專業化審理。加強與香港法律服務業深度合作,建設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同時進一步完善訴訟、調解、仲裁等多種糾紛化解機制,構建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打造知識產權保護高地,探索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管理和執法體制。
第三,強化深港融合的高層協調機制。改變現有自貿區部際聯席會議與粵港聯席會議互相獨立、信息相對封閉的狀態,推動部際聯席會議與香港特區的直接互動,充分發揮高層協調的作用。以金融服務為例,通過高層協調機制,推動允許港資金融機構以“零門檻”進駐,并給予區內的金融機構在利率市場化基礎上開展跨境雙向人民幣存貸業務的資格,按照“定機構、定額度、定監管”的原則率先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推進深港金融產業的深度合作。強化前海深港聯合工作小組的職能,推動加強小組與高層協調機制的聯系,促進小組常態化工作機制的建立,并及時研究解決深港融合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努力打造高層協調、高度授權、高效靈活的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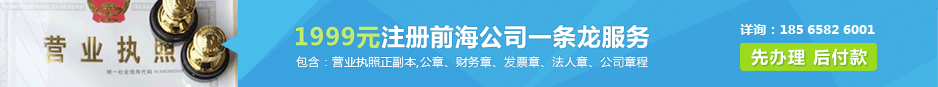
- 推薦閱讀
- 深圳前海管理局辦公址及聯系電話點擊:2747
- 地鐵11號線開通啦!福田15分鐘到前海點擊:1516
- 注冊前海公司營業范圍怎么填寫?點擊:939
- 寸土寸金!填出來的前海點擊:833
- 前海鼓勵類產業企業,優惠稅額達到21.15億元!點擊:714
- 16項新政惠及深圳前海外籍人才!點擊:573
- 想在前海注冊一家公司還需要實際辦公地址嗎?點擊:547
- 前海自貿區環境幽雅 前海硅谷吸引企業注冊點擊:546
- 政策好優惠多港青紛紛前海創業點擊:513
- 香港人前海注冊公司創業偏愛前海夢工場點擊:438